无法回避的考验:乡村文明在断裂?
原编者按: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数千年的乡土社会向何处去?萧条、衰败甚至消亡,难道这真会是它的命运?我们的田园梦、我们的乡愁,难道真会像有些人说的,有一天将无以承载?
随着青壮年大量外流,农村空心化严重,一些地方环境遭到破坏,一些地方公益事业乏人问津,一些地方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社会风气有所败坏、伦理道德有所滑坡。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在社会的巨大变迁面前,面临严峻考验。
但毋庸置疑的是,农业不会消失,农村不会消亡,农民不会绝迹。即便中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将会有数亿人生活在乡村。乡土社会一直是,也将永远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分;乡土文明,哺育了中国,也必将承衣钵开新命,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进程!
如何重建乡村社会?如何跨越乡村文明的断裂带?如何打造新乡村文明?这就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时代命题。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长期关注这一问题,历年组织师生利用春节假期回乡调研,调研成果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2015年, 师生们又写出了100余篇回乡记,从不同侧面记录乡村社会变迁,从各个角度思考乡村社会重建。本期专题我们摘编部分篇目,期望这些文章不仅能一慰读者的 “乡愁”,更能引起全社会对乡村建设的重视与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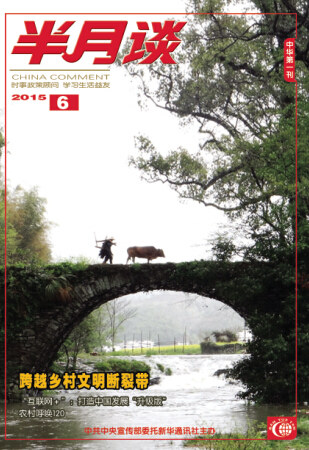
传统沉浮
一块匾:铭刻于心的乡村温情
■ 宋丽朝
姥姥今年90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接生员,一 辈子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贫寒的岁月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乡下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乡邻们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90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 表谢意。
姥姥在农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数十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 会精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产妇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要跋涉数十里路,有时要惊心动魄 地抢救无呼吸的婴儿……
姥姥当接生员是当年组织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听从组织安 排,安心学习。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学得又好又快。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人民公社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 田到户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
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从村前到 村后,从本村到外村,人们只要见到姥姥,大老远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婶子。农民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来答谢,姥姥也不图这个,一句奶奶的呼唤,一个 欢乐的笑脸,就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关于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以前,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 匠来做,于是爷爷为他人“帮工”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 板、修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什么报酬,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我们村的老村医也是这样,他今年已经70多岁,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对手脚不灵便的老人 他都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很多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慰藉,一番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医好一 半。而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困难老人,赊账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接生员、木匠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更 是这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
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的生命,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呵护与关爱。我们出生在 一个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 会。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远离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理性日益占据。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 的到来,钱就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地办到;治病救人也是钱的交换。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这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份 温情渐渐变淡。
可是,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岁的姥姥多年前的善举。与其说这次“挂匾”是为姥姥歌功颂德,不如说它是乡村社会的“乡愁”,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一个仪式:乡土社会伦理空间
■ 高万芹
我的家乡位于鲁中地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孔子家乡比较近的缘故,家里过年的习俗多,规矩也多,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很忙。尤其是大学毕业后, 除了帮助爸妈张罗以外,还要参与各种家门聚会和活动。老妈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忙碌,一直到初六、初七才能空闲下来,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乡,真正 的过年也就是这几天,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磕头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对一个家门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
按照传统习俗,各家门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圆饭后设神位、摆家堂,供祭祀和晚辈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这些神位和灵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这 些供奉的神灵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家门内的男丁要去长辈那里帮忙张罗摆设。神位一般是设两个,天地神位和财神神位,天地神位设在庭院,财神神位设在屋内。 摆家堂主要是摆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宗亲。老人抚养儿女长大便是功劳,死后可以与神一样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家门中的人要通过放鞭炮的仪式送走先人,也意味着过年祭祀活动的结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户还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吃完之后,先在 自己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灵和先人,然后带上鞭炮去家族内摆家堂的长辈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爷爷在同辈中是老大,因此,爷爷在的时候,每年初二我们全 家都会带上鞭炮到爷爷家集合,五服以内的宗亲也都到他家集合。爷爷很喜欢这样的大家庭聚会,五服以内的亲人到场,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听到亲人夸赞他福气 好、儿女孝顺,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大家参与的热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丧葬、先人的忌日,传统的仪式性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这些家族仪式会不会随着农村传统伦理的衰落和老一辈的故去而消失?老妈认为不会,送家堂不该取消,应该被传承。每次送家堂,老妈都很累,忙这忙 那,还一定要我们姐弟打扮得体去参与,好像就是为了让先人和亲人看看我们三个。在她看来,我们姐弟三个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风景,虽然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 大成就,但抚养我们三个不容易,苦尽虽未甘来,却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家门的一 分子,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 就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尘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保佑,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不敬,也 不敢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触怒他们,把灾难降临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保佑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祈祷,这份希望,强大而坚 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泯灭。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 生任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全身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 有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
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
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家门聚会,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 与此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舆论场,优秀的家族成员得到褒扬,有过失的受到批评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释放空 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心扉,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 过度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丧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家门内所有人灌输道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 式。因为它们维系家门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世人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 后也应该被隆重祭奠。
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
■ 杨春滋
农历腊月二十一,妈妈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妈妈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腊月十九亲戚们刚去参加他曾孙的满月酒席。当时老人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很快,妈妈就从亲戚那儿得知,老人是上吊自杀的。
母亲的大伯从小居住在村里,靠种地为生,共养育了两个儿子,是夏姓家族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满八十九岁,又喜得曾孙子,成为 村中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腊月十九,夏家的三层楼房张灯结彩,鞭炮阵阵。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带着曾孙回来了,为曾孙办“满月酒”。由于夏 家在村中的影响,亲友、乡邻都赶来贺喜,共摆了43桌酒席。
当晚,老人向儿子问起曾孙取名的事,儿子告诉他:曾孙姓夏,考虑到媳妇是独生子女,就取了媳妇的姓作为名字的第二个字,代替了家族中本来的辈分 “书”。老人听后非常气愤,当着部分未走的亲戚说:姓夏的生的儿子从来都是依辈取名的,不能乱辈。儿子说:一辈管一辈,只要姓夏,不按辈分没有多大事,现 在好多人都不按辈分起名。由于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越争越急,互不让步。说到激动处,老人骂起儿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儿子觉得没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 老人气得要打儿子……
老人怒气未平,觉得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平时最听话,又喊来孙子,问曾孙的名字是谁起的,怎么连辈分都不依。孙子说:爷爷,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妈。老人一听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孙子……
第二天一早,儿子跑到镇上,请大哥(老人的大儿子)将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气,孙子则驾车办年货去了。腊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发现老人已在楼房客厅穿戴整齐悬梁自尽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亲友们议论颇多。有的说,老人太固执,为争曾孙的辈分,选择自尽的方式,有点极端。有的人也私下指责,儿子、孙子不孝,为 曾孙的辈分闹出了人命,让一个高寿老人不能善终。老人的弟弟们岁数也都不小了,赶来为长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说,“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闹是闹,不能闹 出人命来,这一闹,让侄儿、侄孙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夏家老兄弟们在村里都觉得没面子。
看起来只是姓名之争,其实是家庭中新旧权威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再那么顺从老父亲的 严格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生活,也不想承担宗族责任和义务,只想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亲的眼里,这是忘本、不仁义,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和挑 战,心中难以接受。更深层的问题是,儿孙长期在外打工,接触各种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经和现代生活接轨,他们不再想遵守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明白这些秩序对老人的意义。
这个悲剧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目前在农村广泛存在的观念冲突、情感撞击。传统价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农村 尤其是农村的代际矛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新旧价值的交锋中,人们要面对许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尽快走出这一境地,整合新旧价值,促进代际沟通理解, 确实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处寻找乡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得晚,走得早,过去的乡间文化娱乐活动早已无人问津,什么样的年味才 能满足这些短暂停留的“客人”?摆一张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递烟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扑克,整个待客之道就形成了。旧的文化活动衰败了, 村里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年,而乡村还无法承载城里的文化活动,于是就自发形成了牌文化以消磨时间。
我的村子是单姓村,相对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围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这几年冷清得很。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住在小村 子没意思,不好玩,村子没有生气。然而,在我的村子,人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随时都可以聚众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断。
村里的旧集体活动衰败后,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以打牌为主的新集体活动。以前的活动,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现在的活动,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参与。打工者过年回家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就是通过打牌实现互动。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会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的、有玩 表情的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 流;玩表情的人,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他方观众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打牌也“分群体”,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个别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来 说,男女不同桌,男的玩得凶狠些,女的玩得温柔些,小孩子玩得随意些。
你在那儿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悔恨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却 被封而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显示了神通,发泄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 时间,获得了谈资。在展示与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舆论场,玩得好的会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观众的笑谈,肯为大家打牌出钱出力组织的 人一定十分受欢迎,这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声誉。
在村里,打牌满足着群体性活动的需求,看起来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但是,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村子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

福建平潭白青乡,村民在午餐时聊天 姜克红摄
养老拷问
农民上楼了,老人住哪里
■ 郑晓园
过年回家拜望长辈,吃惊地发现,表叔表婶居然住在了自己搭建的一间简易棚子里。要知道,他们家的房子在去年被征迁,得到3套还建房,有那么多房 子为什么还住在小棚子里?表叔表婶说,新房分给了孩子,我们两个老人住这里挺好。在了解整个事情之后,我知道,他们的“挺好”并非假话。
表叔表婶今年60多岁,有两个儿子,都已经结婚生子。他们家原来的房子非常大,前面是三间厅房,表叔表婶住一间,还有一间客厅、一间厨房,后面 是三层的楼房,顶楼空着,另外两层每个儿子住一层。与无数农民家庭一样,他们的儿子媳妇都外出打工,只有过年回来,表叔表婶则在家种田、操持家务和带孙 子。大家庭就这样有条不紊地运行着。
早在几年前,老家就有了拆迁的动静。由于表叔家的房子很大,亲戚都开玩笑说他们要成富翁了。可是等到拆迁来了,大家庭却开始出现风波。
表叔家最终补偿了3套房子和20万元,新房在区里统一规划建设的还建小区,为同一栋楼的1层、4层和5层。其中,5层为顶层,日晒雨淋的,两个 儿子都不愿意要。两兄弟商量后,分别要了1层和4层,就各自积极装修去了。表叔表婶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好,爬上爬下很吃力,显然没有办法住上5楼,而他们 也不愿意和儿子住在一起。虽然每套还建房是统一的100平方米,两室一厅加一个存储室,存储室可以改成小卧室,变成三室一厅,足以容纳三代人的家庭,但是 儿子媳妇不愿意、老人也不愿意住在一起。
对于儿子媳妇而言,拆迁是他们获得独立住房的一次机会。拥有现代化装修并且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立住房,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新的住房承载了他们从 大家庭中独立出来、建立个体化私密空间和采取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在原来的房子里,虽是大家庭住一起,但老人与儿子媳妇其实是相对分开的。老人的活动空 间是前厅和院子,儿子媳妇的房间则在后面的楼上,而在新的房子里,两个卧室挨着,大家紧凑地住在一起。
对于老人而言,这是个大问题。空间的紧凑会加剧彼此的冲突,因为没有了回避的余地。表婶说,“以前虽然住在一起,但你做你的我做我的,生了气在 自己的房间静一静就好了。要是住在一起,人家给你脸色看,你都不晓得能往哪里去”“你自己住,不讨嫌,再帮他们做点事,他们才会更加喜欢你”。
这场家庭风波以表叔表婶搭建棚屋而告终。他们在距离老房子100米的地方搭建了一个棚屋居住,这又产生了故事。因为是开发区,按规定是不能再新 建房的。表叔表婶先是搭起了一个很简单的棚子,国土所来人查,他们就说是用来存放农具的,还主动缴了几千块罚款。之后两人趁着夜里偷偷摸摸地给棚子添砖加 瓦,今天加根梁,明天挖口井,后天安个门。这项“伟大”的搭棚事业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年多,才成了目前可以住人的样子: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子,摆了一张 床、一个灶,房前屋后是院子,旁边是菜地。表叔继续做着计划,有机会就扩展旁边的空地,表婶对现状则很满意,“已经够我们住了”。
表婶颇为得意地告诉我,很多老人都羡慕他们有个棚子,“老人都不愿意住在楼房,一大把年纪上不动,没有地种、没有柴火烧,还不能随地吐痰,每天 对着巴掌大的地方,真是活遭罪”。这些老人带着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上了楼,没过多久,小区里的花坛和零碎土地都被开垦成小块菜地,楼下也架起了不少火炉, 每到饭点就炊烟袅袅,熏黑了墙壁。这些“杰作”,引来了小区里年轻人的抱怨和骂声,儿女们只好红着脸吼回自己的老人。
与这些老人不同,表叔表婶用棚子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尊严。现在,他们的儿子媳妇照样出去打工,两人则住在棚屋里,种上粮食种上菜,吃喝不 愁,除了房子比以前小,其他什么都没变。这样的生活对他们而言,的确是“挺好”。但不好的地方也有三点。一是就两个人住在那里,难免孤单,虽说和儿子媳妇 住在一起会有矛盾,但住远了(小区距离老房子10多里),见不着也会想念;二是现在还能动,什么都好说,再过几年,老了不能动了,跟儿子媳妇住得这么远, 就算他们想照顾都没有办法;三是住得不安心,不知道国土所还会不会来撵他们走。
表叔表婶说,等到老了不能动了,还是不愿意跟儿子媳妇住在一起。理想的情况是,政府在小区附近盖个老年公寓,老人住进去,一起玩、闹,再每家老人分点菜地,能动就自己动,有事就叫子女。
表叔表婶的理想其实也是千千万万上楼老人的诉求。所谓“老有所养”,前提是老有所居。而这“居”,并不仅仅是简单的物质空间,而是承载了代际关系、生活方式诉求以及“如何老去”时代命题的社会空间。

养老:土地比儿子更可靠
■ 王海娟
由于祖祖辈辈都是依靠家庭养老,“养儿防老”成为农民生育子女的动力之一。但在农村的现代化变迁中,不少农民认识到子女不再是依靠,真正给老年 人依靠的是脚下的土地。据村里的老村干部讲,“全村100多个老年人中,由儿子赡养的很少,老年人一般靠耕种土地和国家养老金生活”。在我所居住的湾子里 有8个老年人,这些老年人都没有靠儿子养老,而是“以地养老”,在农民眼中,土地比儿子更可靠。
以我爷爷为例。我爷爷今年83岁,生育有3个儿子和3个女儿,是我们湾子里年龄最大的老人。爷爷去年耕种2亩地,种植了玉米、红薯、油菜、棉花 和各种蔬菜等,日常生活所需几乎全部来自自己耕种的土地,可以称得上是自给自足。爷爷还利用杂粮和菜叶养鸡鸭,满足自己的肉蛋需求。由于爷爷年龄较大,近 几年无法种植水稻,食用的粮食是存粮,去年存粮用完后爷爷到别人田里拾到500多斤稻谷。
爷爷耕种土地还能够获得少量的货币收入,如出售棉花和鸡蛋鸭蛋等,土鸡蛋每个1.5元,去年爷爷出售鸡蛋获得500元收入。衣服和鞋子由女儿 买。爷爷需要定期购买的只有猪肉、烟、盐和洗衣粉,出售农产品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可以满足日常开支。爷爷的货币收入还有孙子孙女每年给的零花钱1000多元 和国家每月的高龄老人养老金120元。除了医疗费用和人情开支外,爷爷还储蓄1万多元。在家乡,有钱去集市买小吃是老年人富裕的象征,每天去集市逛逛,买 自己喜欢的小吃是爷爷的“例行公事”。
土地给爷爷提供的不仅仅是生存所需的物质,还有尊严和老有所乐。爷爷奶奶居住在老房子里,不需要依靠子女生活,不需要低声下气地讨好子女,通过 经济独立维护了自己的尊严。虽然爷爷只耕种2亩地,只需要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劳作,但是爷爷每天都要去地里转转,拔拔草,看看庄稼的长势,就像是照看自己的 子女。在播种中种下希望,在收获中获得喜悦。劳作对老年人而言,不是负担,而是休闲,这或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休闲农业。
能走动的老年人多多少少都会种点地,养几只鸡,种点蔬菜,加上国家的养老金,养老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在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尚有待完善,“养儿防 老”作用退化的情况下,土地对于农村的意义需要全面考量。不能随意以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名义剥夺农民种地的权利,否则农村老人面临的是更无依靠的未来。 每个家庭都有老人,每个人都会老去,莫让农民老无所依。
周堡村热闹的老年人协会
■ 夏柱智
周堡村是湖北省阳新县一个偏僻的小村子。村里老年人向我说起村里在去年12月办了一件好事,就是新村委班子建了一个老年人协会,成为老年人休闲 娱乐的中心,老年人去打小麻将,打不要钱的扑克,打乒乓球、羽毛球,下象棋,看书阅读,围在火炉边聊聊天,“没有事情到协会去坐坐”成为老年人生活的新模 式。
村主任柯友安说,去年当地政府用扶贫资金建起了村委会大楼,为了满足村里老年人一直以来的强烈愿望,村委会班子利用闲置的房屋,并向政府申请了2万元财政资金,购置桌椅板凳等硬件设备,建起了老年人协会,并初步建立了管理制度。
在协会,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门外的一张钢化玻璃乒乓球桌。球桌是由村里出资,村干部用车拉回来的。打乒乓球成了大家的最爱,当然羽毛球也少不了。平常有许多留守儿童和老年人一起在协会玩,假期或放学后在那里展开乒乓大战,玩得不亦乐乎。
走进协会大厅,里面大概有五六十平方米,可以放下十几张桌子。协会有专门的书柜,放了各种书籍,儿童类的、生活类的、军事类的,还订阅了一些报 纸。房子中间安放了一个新式炉子,冬季每天准时烧炉子,非常暖和;夏天则准备了2台吊扇,保障冬暖夏凉。许多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里面玩,很美好的乡村娱乐 画卷……
老年人协会的日常管理由村委会聘请的陈芳谷老人负责,他今年74岁,是非常积极的老党员。协会要为老年人准备干净温暖的环境,就需要有人值班, 日常事务包括管理财务、烧炉子取暖、烧开水、打扫卫生等。报酬不高,一天10元。陈芳谷老人在冬天一般是早上七点半过来,晚上五点半回去,最晚的时候六点 多,一直等到老人们都离开。
除了本村人,邻村的老年人也经常来玩。军山村刘应喜老人,60多岁了,非常喜欢这里,一般是骑电动车过来。外面来走亲戚的老人也愿意过来玩,附近太平村、樟树村、三洲村的不少村民也慕名而来。
周堡村是家乡农村的特例。近年来,普遍的村委会大楼建设带来的是普遍的房屋闲置,有的村庄村委会大楼甚至常年不开门。如果用这些闲置的房屋建设老年人文化活动场所,肯定会受欢迎,大大增加农民的精神福利,但这一般没有被列入农村文化建设的重点。
实际上,建立和维护老年人协会不需要太多资金。在周堡村,财政给了2万元启动资金之后,协会基本是依靠在里面玩乐的老年人自愿交费来维持。到这 里玩的老年人普遍愿意给钱,以维持这个协会。按照前几个月运行的情况看,每天能收入30元,基本可以满足管理人员工资、水电费和取暖费等开支。
对于老年人,这个协会是他们的精神家园。老年人说,到这里来寻开心,没有负担,要是到别人家闲聊娱乐,一是怕打扰别人,俗话说“热天不挡别人的风头,冷天不挡别人的火头”,现在都是新房子,到别人家去多了,人家会有意见;二是不够热闹,缺乏集中在一起娱乐的气氛。
周堡村农民说,建设老年人协会,是继国家普遍给老人发放养老金之后办的最大的实事。国家给老人发放养老金,解决了老年人的零花钱问题,老年人不 必看子女眼色,有虽然不多却很顶用的闲钱来娱乐;老年人协会的创办则使老年人有一个集中的去处,在这里可以互相取暖,在闲聊、打牌中幸福悠闲地度过老年时 光。

微信扫一扫|长按识别,进入读者交流群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