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劳动者的文化主人地位
刘润为

1942年,中国文艺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如果说《讲话》是一次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那么,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就是在这一光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创新。
新在哪里呢?新就新在争取广大劳动者的文化权利上,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中国阶级社会几千年,什么时候有人把劳动者当作文化的主人呢?从来没有过。当然,流传下来的作品,也有劳动人民创造的,如《诗经》中的《硕鼠》、《伐檀》等等,但是少得可怜。在文人那里,同情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劳动者心声的作品也是有的,而且不少。仅以诗歌为例,就有杜甫的“三吏”、“三别”等等。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是自觉地把立足点放到劳动者一边,自觉地为劳动者服务的,而只能说是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所谓人民性,无非是对广大劳动者有一些同情或理解而已,还远不能说是在立场、思想和感情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当然,这里有着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白居易在理论上也提出过“唯歌生民病”,但他不是为了唤起劳动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是“愿得天子知”,进而实行一点儿“仁政”。在中国,真正把广大劳动者置于文化主人地位的,是觉醒的劳动者自己,是觉醒的劳动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那一天起,就一直探讨人民文艺的问题。李大钊、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这方面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过艰辛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求实地说,这些理论还不成体系,这些实践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自觉的运动。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总结中国进步文艺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劳动者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核心,就是人民群众的主体观。具体地说,就是认为历史是劳动者创造的,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文艺,不但要把劳动者作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对象,而且应当自觉地为实现劳动者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根本利益而存在而发展。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贡献,就是在继承鲁迅等左翼作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把《讲话》精神落到了实处,落到了千百万劳动者的心中,落到了人类文艺史的丰碑之上。
据有关文献,当时贺敬之未能参加座谈会,但他对会议和《讲话》的热情丝毫不亚于与会同志。他听了《讲话》精神的传达,感到简直是如沐清风霁月,特别是对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无条件到生活中去等观点,感到既非常亲切又非常新鲜。于是,他以如饥似渴的心情,见到与会同志就打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在听周立波复述关于“普及与提高”的内容时,贺敬之问:“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这是不是和民主集中制一样,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的指导下民主?”周立波兴奋地肯定说:“你理解得很好,就是这样的。”在包括贺敬之在内的未能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要求下,毛泽东又为他们作了关于小鲁艺与大鲁艺的重要讲话,这使贺敬之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有了更直接更深刻的感受和理解。
那么,贺敬之为什么会对《讲话》表现出如此巨大的热情呢?用精神现象学的话来说,这是由他特定的“先在结构”或“前在图景”决定的。大家都知道,贺敬之出身贫苦,自幼就培养起深厚的劳动人民感情和鲜明的被压迫阶级立场,这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如《北方的子孙》、《夏嫂子》、《儿子是在落雪天走的》、《红灯笼》、《小全的爹在夜里》、《黑鼻子八叔》等等,真实地记述了旧中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境遇,传达了他们的愤怒和希望,表现了他们为改变自身命运而自发进行的反抗和斗争。但是,在《讲话》发表之前,应当说,贺敬之的这种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和创作倾向还处于朦胧的、朴素的、稚嫩的阶段。为什么要为劳动群众创作,怎样为劳动群众创作,正是青年贺敬之苦苦探索的问题。《讲话》正好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他的思想理论的需要。这恰如久旱之逢春雨,接踵而来的自然是生机勃发、花团锦簇。
《讲话》对贺敬之的影响,一言以蔽之,就是促成了诗人在思想和创作上的自觉,这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战争的生活,在与北方广大农民和八路军战士的共同生活中不断实现思想的升华,不断进行生活素材和思想感情的积累;二是能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生活、分析生活,把握生活的本质方面;三是在艺术形式上,自觉地以开放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探索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三个方面的自觉,使诗人的创作发生了质的飞跃。
创作于1943年的歌词《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陕北农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成绩。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民族化、农民化、陕北农民化,已经成为贺敬之自觉采取的情感方式和语言形式。用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这——就是这支歌传唱半个多世纪而且还将继续传唱下去的秘密所在。1947年,贺敬之深入冀中农村参加土改。由于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那里的贫苦农民焕发出高昂的革命热情。父送子、妻送郎,踊跃参军打老蒋,成了当时冀中农村热火朝天的动人场面。诗人深入其间,从这里汲取诗情、把握诗魂、创造诗境,于是就有了长诗《搂草鸡毛》。这首诗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喜剧情调,表现了各村青年你追我赶争当参军模范集体的精神风貌。“搂草鸡毛”,是河北农村的方言。“草鸡”,即母鸡,指在风险和考验面前退缩的人。“搂草鸡毛”,就是要撸一撸你的毛,刺激你一下,让你振作起来,变成雄壮勇敢的公鸡。不用多说,这首诗是用锤炼了的农民语言传达了翻身农民的情绪。这是诗人深入生活、深入翻身农民内心世界的艺术回报。
当然,最能代表贺敬之学习《讲话》、实践《讲话》成果的,是他与丁毅以及其他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歌剧《白毛女》。
首先,它实现了外来艺术样式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一是指它所反映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完全是中国的、中国农民的。二是指本文结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它不像西方那样将悲剧推到悲惨的极端,而是既反映主人公遭受的苦难又升起光明和希望。这既是当时中国农村的真实,又切合中国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欣赏习惯。三是指它的语言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式的。四是指它的曲调是富有民族特色、民间特色的,如著名的《北风吹》,就是在改造民间曲调《小白菜》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它正确地把握了当时的阶级关系:由帝国主义势力、官僚买办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同盟织成的剥削网,是中国农民罹遭苦难的根源,农民阶级是旧中国一切民族灾难的最大承担者。
再次,它充分表现了中国农民作为天地生人,酷爱生活、酷爱自由的性格特征和为摆脱剥削压迫而自发进行的抗争。
最后,它揭示了中国农民改变命运的决定性因素,即八路军——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正是因为《白毛女》以其鲜明的民族形式,对旧中国农民的生存境遇、意志情感和解放道路进行了高度典型化的艺术概括,所以具有最彻底的人道主义内容,从而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极易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来者。
没有《讲话》,就没有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别开生面的创作;没有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别开生面的创作,就无从确证《讲话》的伟力和魅力。在彻底的劳动者的立场上实现理论与创作的完美统一,这就是《讲话》与贺敬之等一大批革命文艺家的最根本、最内在的联系。
实践《讲话》精神,为劳动者写书、演戏、唱歌,本是好事、天大的好事,可这种好事并不是所有的文艺家都能坚持到底的,尤其是在西方文化压迫到来的时候,各种“实惠”频频抛出媚眼的时候,更是如此。贺敬之的可贵之处在于,既然认定《讲话》是余心所善、民心所善,就“九死其犹未悔”地坚持下去。无论是在创作实践还是工作实践中,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处于逆境中,他都能坚持《讲话》精神不动摇。《回延安》、《放声歌唱》、《桂林山水歌》、《中国的十月》等等建国以来的名篇,就是明证。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他不计毁誉得失,挺身而出,与种种否定《讲话》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个革命文艺家最可宝贵的性格。可以无愧地说,《讲话》精神滋养了贺敬之的一生、改变了贺敬之的一生、激励了贺敬之的一生、成就了贺敬之的一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进一步发展了《讲话》的思想。他说:“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总之,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能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事实证明,广大劳动者如果不能在文化上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就不能在经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权利。进入新时期以来,社会主义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不必讳言,在文化领域的某些环节、某些方面,劳动者的文化权利已经被部分地甚至全部地剥夺。为数不少的文艺家根本不屑于表现劳动者作为创造历史主体的形象,根本无意去传达广大劳动者的意志、愿望和情感,更有甚者,竟然把美化剥削、鄙薄劳动、嘲笑贫穷、阿谀富贵当作一种自鸣得意的时髦。须知,这是连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中的明白人都感到羞耻的粗鄙行为。这种倾向如果任其泛滥下去,势必导致广大劳动者一切权利的丧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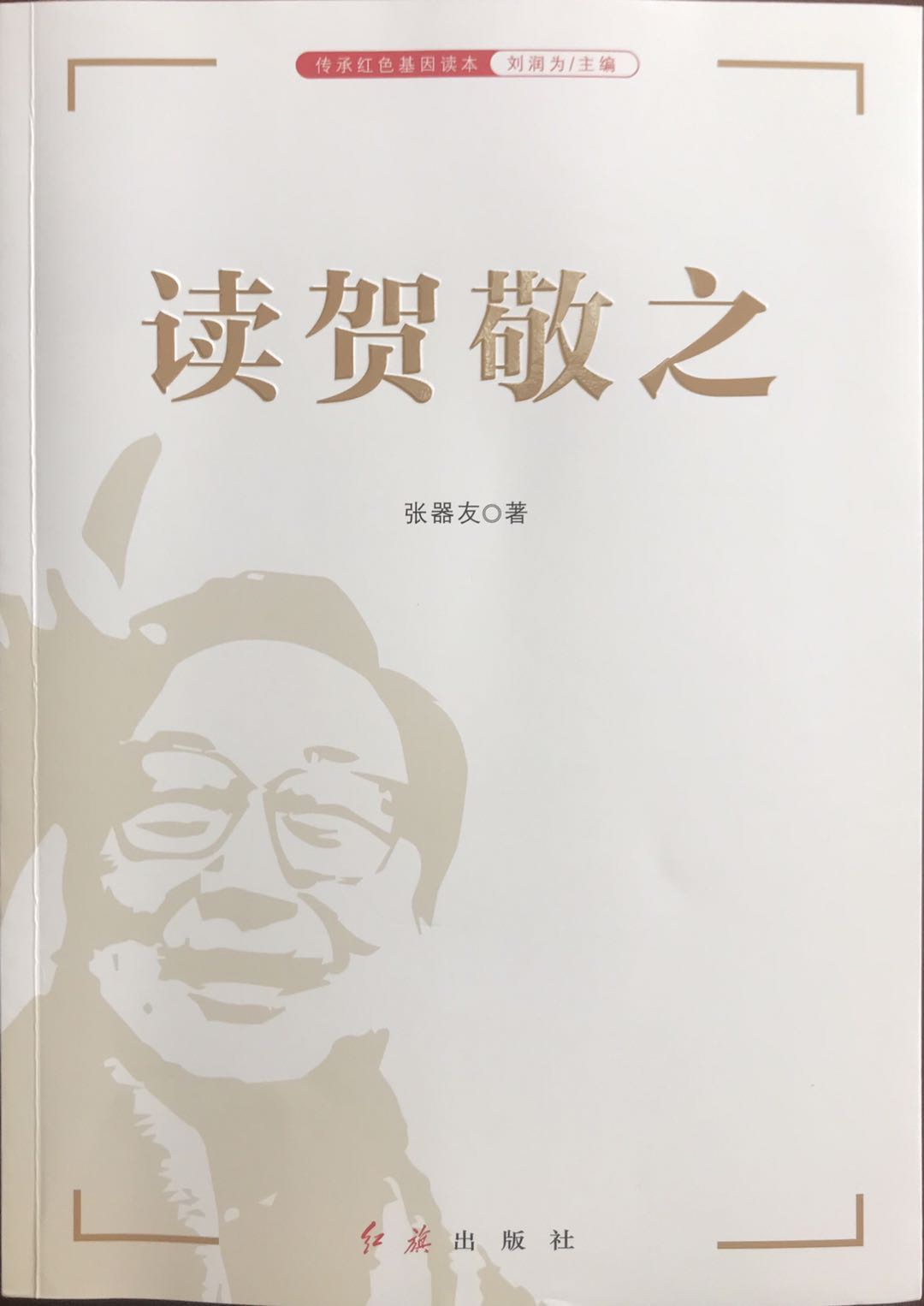
由此可见,研究贺敬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解剖典型回答社会主义文艺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大问题。张器友教授长期致力于贺敬之研究,眼界开阔、学风严谨、学识渊博,颇多建树。《读贺敬之》就是其研究的集大成者。读这部书,我们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明白怎样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怎样在思想感情上与人民群众融为一体,怎样在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实践中进行生活积累与情感积累,怎样以个性化的形式创造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在新时代排除干扰,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所以说,这部书不仅回望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2019年5月11日
(本文是为张器友《读贺敬之》一书所写的序言,此次发表内容上略有增添。该书于2020年1月由红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