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编者按:八十年代,一位化名“潘晓”的青年人给《中国青年》去了一封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萧条异代不同时,那代在人生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找寻不到意义的青年的后辈,如今也发出了相似的感慨。
“中产”:熟悉的陌生人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个词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虽然对工农阶级心向往之,但也深知自己无论从经济基础还是从文化趣味上来说,都无法回避小资的属性,不敢腆着脸自称为工农阶级一员。于是,讨论“中产”势必带着对自己的解剖。然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处其中的我却很难肯定地说,自己对“中产”已了如执掌。
30多岁的我,生活在上海,工作在学校。如果我算“中产”的话,那我的“产”从哪里来呢?仅靠自己的工资,其实连在学校周边租房子都难,加上父母的经济支持,才过上了靠自己的劳动“衣、食、行”的生活。如果对父母的支援来个釜底抽薪,那就只能和伴侣一起与别人合租了,“衣、食、行”也得更加地精打细算。那么,我还算中产吗?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曾提到过我们这些“中间等级”: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
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那个年代,还没有“中产”这么“高级”的称呼。“小资”(petite bourgeoisie) 倒是有的,指的就是上文中的那些小生产者、小商人和农民。时过境迁,如今,中国大陆语境下的“小资”则更多地指向城市、白领、脑力劳动和个性品味等意涵。
“中产”这个概念恐怕出现得晚一些。二战之后,也即美国制造业在二十世纪头几十年里赶超了英国之后,美国又把制造业转回给战后亟待经济复苏的西欧各国。西欧等国家通过凯恩斯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恢复经济,福利国家制度和工团主义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制造出一种欧洲工人阶级整体白领化、中产化的现象。没过多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资本空间的再次转移,拉美、亚洲中的巴西、日本、韩国等国的制造业的工人阶级不断壮大。而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欧等国则经历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中产阶级崛起。混合了技术工人和非制造业部类的专业技术职员成为了这一阶级的主要人群。
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等书中批判性地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分析方法,美国的“中产”在现实生活中处于政治中立、犬儒、后卫的位置。中产即便投入到社会斗争的场域中去争取权利,也都很难在一个无产阶级消灭剥削,争取全人类解放的框架中去实践。在这一点上,中产阶级的“去政治化”是无疑的了,总是显现出“摇摆性”来。后辈学人对中产的整体分析和判断似乎并没有在本质上超越出马克思他老人家的那段评述。马克思既揭示了“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的反动性,也提出了他们如果和无产阶级走到一起的话,是基于怎样的条件。米尔斯对二战后美国的新中产阶级做了更为充分的分析,认为这一可怜、困顿的阶级实际上是向无产阶级更加靠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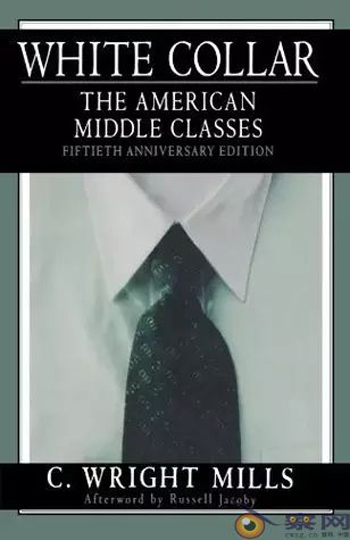
(图为《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封面,图片来源:goodreads)
那么,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又是怎样的呢?如今,中国大陆不仅有一个数量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在第三产业中就职的小资、中产,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如果要对中国大陆的中产阶级做一个深入的分析,本应先深入历史。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先从自身的经验和身边同龄人的经验感知入手,提出一些观察来。那么,首当其冲的朦胧感觉是,“中产”的内部还需要进一步划分,划分为搭上大资本顺风车的中产和搭不上却想搭上的中产。在我的经验中,我所熟悉的“中产”更多的是后者。
经济:想得到、怕失去
作为稍有资产者,最怕的其实是资产的缩水,被抛入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但是,纵使经济学、金融学学富五车,如果无缘与大资本挂靠,就难以把自己拔到鸟瞰全球资本构架的高度上看清所有的机遇和陷阱。手头有了点积蓄,可以干嘛呢?放银行?只是让资产缩水放缓,利息远比不上通货膨胀,长期来看必然贬值。做股票?股市不景气已久矣,套牢的人已多矣。买美元?买吧,一年只能换5万,时间一过,行情早就变了。国内的房子是买不起了,去海外投资买房?等澳大利亚有机会炒房的消息传到吾等“中产”大众的耳朵里,黄花菜都凉了,筹资、验证渠道的可信度都来不及。去农村购地?你拼得过大资本么?小产权房敢买吗?投资给民间融资机构?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走向赤贫堪称最快。

(图为A股界面,图片来源:网络)
其实,吾等中产再动足脑筋也是白搭,这年头,其实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加班加点挣来的辛苦钱贬值。吃光用光拉倒?不行!还要想着一家老小的医疗费、养老费和教育费。突然来个大病,或者其他什么变故,该怎么办呢?还是放银行吧,几害相权取其轻。
又想起了《共产党宣言》里的描述: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放到当下的情境中来看,不光工人领到了工资之后,有一群人向他们扑过来,中产阶级在领到了工资之后,也有一群人扑过来:房东、房贷、股市财经“学习班”、健身房、(自我标榜)的健康食品、各类海淘网站、高端MBA班……不过,现实的逻辑恰恰是,这些扑过来在资本的价值实现领域里夺走中产阶级手中现金的各路恶煞并不引起中产的反感和警惕,反而受到中产的欢迎和追捧,因为这些扑过来的恶煞在吾等中产的理解中反而是神通广大的仙人。还房贷虽然痛苦,但可以巩固自己中产的身份,股市财经班虽然巨贵无比,却或许是通往大资本所打造的“挪亚方舟”的捷径。一边,资产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缩水,一边我们要与时间赛跑,努力寻找刺激资产保值、增殖的妙法。
天上不会掉馅饼,让资产保值、增殖可不是慈善救济,背后首先是代价:先要付费。针对中产这一窘境,倒是催生了一个财经领域的配套服务业,成全了一批富人,让他们抓住了商机,越加富贵:各类培训班,就连不差钱的吴晓波也抓住了商机,将自己每日清晨的感想包装一下,变成语音,卖给想资产保值的中产、小资。无论股市、炒房等投资领域是跌是涨,卖此类知识都不会亏本。不断描绘只此一个“挪亚方舟”的图景,于是,中产的梦想填满了他人的钱包。
怕失去、想得到,成为中产生活的基本逻辑,两方面组成一个怪圈,成为中产生活、工作的行动依据。对自己私有财产的无可奈何的担忧,转化为投身保财产促增殖的动力,以实际行动落实“想得到”的愿望。而“想得到”的野心说穿了并不大——在这个不上天堂就意味着下地狱的年代,与其说“想得到”是一种做资本家的白日梦,不如说是担心自己的不作为让自己跌落成为无产阶级的焦虑感。在非此即彼的逻辑中对投资理财、社会晋升的狂飙突进,掩盖的是深深的无奈和无力感。现在,中产的追求已经不再是“财务自由”了,这个梦几乎已经破碎。取而代之的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尽量止亏保值。然而,算计了半天才发现,算上父母的资产,充其量也只有一只鸡蛋,而控制着篮子,调节篮子高低的阀门并不掌握在中产手中。
肉身:个体承重
和身边的女性朋友们聊多了,就会发现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达成了一个共识:小时候,我们特听父母的话,最后发现,那些话是有时效性的,居然并非普适真理。最典型的场景是,父母们对着自己的宝贝闺女说,孩子啊,你要好好念书啊,不要把心思都放到打扮上去,好好地把心思收回来,靠自己的能力,以后的路不会差的。等我们长大了,发现,在这样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里,在这样一个“宁可坐在宝马里哭”的年代里,父母根正苗红的话,已在风中凌乱。我们的确靠死命念书的“个人”奋斗在城市里找到了看上去挺好的office工作,但是却买不起房子。我们千辛万苦没有剩下,把自己嫁了出去,却发现生孩子是要影响饭碗的。我们在家庭和事业之间总算找到了平衡,但却发现自己已经累垮了,生病了。我们谢天谢地感谢还有社保,比工农阶级的同龄人幸福多了,却又发现重返社会角斗场的时候,已经落下一大截了。于是,被抛入无产阶级的危机感又冒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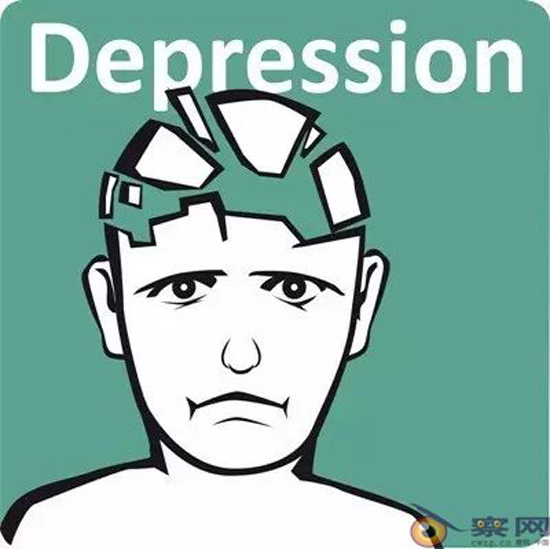
(图片来源:网络)
在不知不觉中,抑郁症、抑郁症倾向在耳边成为了高频词。聊天、排解、慰问……尽力帮助友人之后,也没有别的办法再帮了。再帮下去,自己的工作也要搭上。无奈只得硬下心来不主动联系。身边的朋友们以为,像我这样的职业,在学校里只要把课上完就成了,轻松愉悦。隔行如隔山的我们互相一合计,才发现其实哪行哪业都是一样的:不进则败。高校非升即走的规定,早就不是新闻了。当公务员是好差事吗?时间长了,总在一个办事员的位置上,会遭人排挤,而且,收入也堪忧。想晋升吗?得获得领导垂青先当秘书,鞍前马后,不分昼夜,多面手是锻炼了,但是专业性内涵极低。在外企是否好一些?如果一直在一个位置上,没能晋升到核心高管,就不要怪迅速崛起的后浪把你拍到岸上去,晾在一边。核心岗位只有那么几个,逐鹿中原?
末位淘汰,形式千变万化,而逻辑亘古不变。中产阶级在个人发展和资产保值上遭遇到的尴尬境地是一致的:不想当老板且没能力当老板的工人,连当工人的资格都会被剥夺。不可否认,无论如何,是比工农兄弟姐妹们幸福多了,但身处的生存逻辑,似乎是一样的。我们被无形的手区隔开来,都以为对方的行业才是轻松的、高薪的,互相一通信息之后,才明白,各行各业的逻辑都是类似的……究竟是谁把我们逼迫到你升我走,你死我活的境地呢?
身边除了抑郁倾向的朋友增多了,生病与辞职休养的朋友也增多了。总是会听说,那个谁谁谁,体检查出了甲状腺XX要开刀,就辞职不干了,在家里休养。又有某个谁谁谁,怀了二胎但高龄产妇身体堪忧,辞职不干了,已经退休的父母又得去找活儿干了,为了多挣些奶粉费。朋友说,在外企工作,企业如果知道你生病了,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会赶紧让你回家,生怕企业要承担什么责任,或者怕有些病会传染影响其他员工。与之相呼应的是,亲友们关心的话语也越来越多:身体最重要,其他都是假的,工作上的事推不掉就应付应付吧,不要太认真了。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知道,自己调节。
是的,似乎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的处境负责,除此之外,你无法也不应该去找其他的责任主体。中产在政治上的消极和在经济上的精神压力已经以个人重负的方式呈现了出来。所有外在的问题只能通过个体坚韧的精神力量来解决,只能通过个体的“偷懒”、“放一放”、“应付”、“看开点”、“事业心不要太重”、“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乃至“辞职”来自我调节。
人生的路,要怎样走?
中产该如何自救呢?一九八零年代,有一位笔名潘晓的年轻人发出感叹: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那一代的年轻人是我们的父辈。当代中产的形成离不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语境。历史语境不同,但是问题似乎依旧有效。在我的经验中,被誉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被批评为政治上保守的中产,其实是享受着一定程度的舒适生活,而背负着沉重的肉体与精神压力的群体。中产的身上充满着矛盾:死要着中产的面子,活受着资本剥削的罪,维持自己的小圈子,奋力争夺大资本的船票,害怕成为无产阶级。马克思所言“维护他们未来的利益”中的“未来利益”实在是看不清楚,还是大资本的船更容易理解。

(图为刊登“潘晓”来信的杂志《中国青年》,图片来源:网络)
但是,也有一些中产意识到了自身生活的困境,探索一些新的自救、互助的形式。比如,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辞掉IT工作,返乡种植有机蔬菜,在乡村中扎根的;还有一些在搞自己的读书会,想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再有一些,积极参与各种志愿者活动,互帮互助。在这些尝试中,我们走出了第一步。我想,我们更要突破自己小圈子的利益共享和利益诉求,从更广阔的层面去理解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打破人群之间的隔膜,发现彼此其实在同一个位置:摆脱压榨,建设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