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直以来,美国梦的核心是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比起欧洲,美国人比较不相信所得重分配的政策。他们相信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但这个美国梦已经彻底破碎了。如今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分明,且人们越来越难改变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儿女更可能致富,穷人的子女越来越难翻身。

一
1931年,一个叫做James Truslow Adams历史学者发表了一本书叫作《美国史诗》The Epic of America,在最后一章他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做“美国梦”,意思是在这种社会秩序中,每个人都可以依据他们的内在能力达致他们应有的地位,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或位置。
一直以来,美国梦的核心是机会平等,而非实质平等;比起欧洲,美国人比较不相信所得重分配的政策。他们相信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
但这个美国梦已经彻底破碎了。
“在1950 年代,我的家乡俄亥俄州克林顿港(Port Clinton)彷彿是美国梦的体现,不论出身背景为何,所有孩子都有合理机会发展。”“然而半个世纪之后,克林顿港的生活有如美国人的恶梦,生命的轨迹将小镇一分为二,社区里弱势家庭的小孩根本难以想象那些天之骄子的未来。”
这是哈佛大学政治学者罗勃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最近一本新书《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Our Kids: 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开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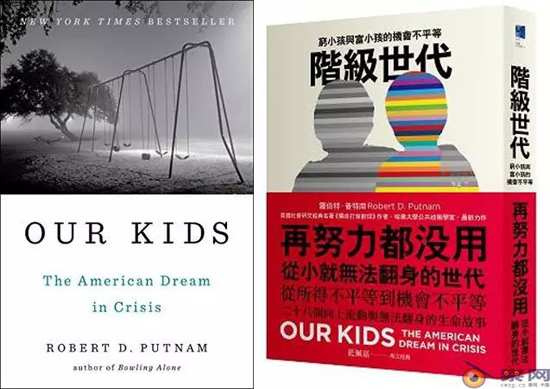
▲ Our Kids,台版译为《阶级世代》
普特南出生于1941年,见证了战后二十年后美国迅速繁荣又能维持相对平等的年代。而这本书讲的不仅是克林顿港的故事,也是整个美国的故事。
克林顿港这个小镇在1950年代是整个美国的缩影:经济与教育迅速扩张、所得相对平等、社区与学校的阶级隔离不大、阶级不是通婚与社交的阻碍、市民参与与社会凝聚力也很高,中下阶层小孩在社会经济阶梯上往上爬的机率源源不断。在这里,虽然确实有人有钱有人没钱,但两个家庭的小孩可以一起做朋友,且后者有机会往上爬──普特南的高中同学们大部分都比父母的学历更好、社经地位更高。
意思是,从社会流动的意义来说,美国梦并不虚幻。
然而,“社会流动率似乎在这几年不断滑落,让美国梦破碎。”“克林顿港半个世纪以来的故事,正如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工人阶级崩溃的历史,也见证一个崭新上层阶级的诞生。”
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趋势开始扩大,先是中产阶级向下滑落到底层,然后是所得顶端的人不断拉大与其他人的距离。不平等快速增长的原因,学者有不同解释,包括全球化、去工业化(如克林顿镇上的大工厂到70年代砍了一半员工,1993 年终于关门)、科技改变、政治与政策(如对工会的打压、对富人减税)等。有些是难以抗拒的结构趋势,有些是政治斗争的结果。
如今的克林顿港,有钱人住的区域和其他人明显不同,他们的生活境遇、下一代的成长机会,也和中下阶层截然不同;从1999年到2013年,生活在贫穷线的小孩从10%上升到40%。对这里和全美其他的蓝领工人社区来说,工资是停滞或下降的,过度用药的人数增加,犯罪率增加,离婚率增加,单亲家庭不断增加。尤其,越来越少人会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社会经济地位与自己不同的人;美国社会沿着阶级界线而分隔的情况十分普遍。
如今的社会,阶级越来越分明,且人们越来越难改变自己的命运:有钱人的儿女更可能致富,穷人的子女越来越难翻身。
二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Angus Deaton)和凯西(Anne Casey) 在2015年发表一篇论文显示,从 1999到2013年,45岁到54的中年白人男性的死亡率是增加的,尤其是在教育程度低的人当中更为严重。他们的死因主要是自杀、药物中毒和酒精导致的肝病。
这是一个奇异的状况,因为在其他国家,或者是美国其他群体中,死亡率都是下降。
对保守派来说,这些现象的解释是自由派政策的结果:一方面是道德败坏,加上人们缺乏宗教信仰和稳定的家庭结构,另方面是社会福利使人懒惰和丧志,养成一种对政府的依赖。但问题是,如果这真是原因,为何更多社会福利或者更开放的欧洲,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另外一种解释是因为美国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多中产阶级向下沦落到底层,而越来越多底层工人陷入生活困境。知名经济学者Branko Milanovic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全球不平等》,他的研究证据表示,全球化让开发中国家的劳工阶级所得上升(尤其中国),让全球最富有的顶端阶层更富有,对工业化国家内部来说则是不平等越来越严重,中产阶级严重消失。
但问题是,就平均所得来说,中年白人还是高于黑人或拉丁裔,失业率也没有他们严重,但为何独有白人出现死亡率增高的现象?
Deaton自己在接受访问时说,其原因是因为“中年白人失去了他们对生活的叙事”,意思是,这群白人曾经如此相信美国梦──亦即美国这个社会的机会是开放给所有人的,只要你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但现实,他们的生活水平远低于他们的预期,也低于他们父辈那一代。
因此,他们自我放弃,用药物、酒精、自杀来面对生活困顿,或者在政治上,支持那些民粹主义的候选人。
三
罗勃普特南的前一本书是《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退和复兴》(Bowling Alone)(2000),此书是脱胎于他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主要论证是美国公民社会和公民精神越来越衰落,越来越少人属于地方的协会。这本书让他从一个哈佛学者,变成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上遍各大媒体,甚至被总统克林顿邀请去戴维营分享。
对政治和社会学界的人来说,他原本就是一名重量级学者。他在1993年出版的著作《让民主运作》(Making Democracy Work) 轰动一时。(那时我正好在大学读政治系,此书确实是必读。)这本书讨论的起点是意大利北部比起南部有更成功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他们透过数据和历史叙述来分析,因为意大利北部一直有比较强大的自治传统、蓬勃的公民社会或所谓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因此导致如今南北不同的发展。社会资本是本书的一个关键概念,依据普特南的定义是“民间交往的网络和规范”,社会资本越强,社群成员彼此信赖度越高,民主和经济都会发展得较好。
这个理论呼应了更早之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的经典观察:美国民主之所以可以良好运作,是因为有大量的、活跃的市民组织构建起的强壮公民社会。
《独自打保龄球》可以说是把《让民主运作》的概念移植回美国,并且是一种对托克维尔的当代对话。1995年的那篇论文之所以引起很大回响,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很大关系。克林顿上任之初,就呼吁美国要恢复志愿者精神;而学者Nicholas Lemann则在《纽约书评》强调,因为克林顿要把民主党带往中间走,要弱化大政府角色,所以很强调市民的自愿参与精神,因此普特南的理论很能契合他们的焦虑。同一时期在学术界,社会学者如Amitai Etzioni也开始畅谈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人们都在寻找重建美国衰败社区的出路。
《我们的孩子》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深化了《独自打保龄球》的讨论:普特南把阶级分析放进社区中。毕竟,公民社会和社会资本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社区衰败最严重的地方就是那些贫穷社区,而这些社区崩解的根源就是高失业率、高犯罪率、破碎家庭。或者反过来说,是严重的社会不平等,让美国的社会资本沿着阶级不断弱化。
有趣的是,如果《独自打保龄球》符合九十年代克林顿时代的政治和知识气氛,这本《我们的孩子》则正好呼应奥巴马时代的核心议题:经济不平等。甚至预测了特朗普的兴起。这是学者的敏锐?
四
普特南在这本《我们的孩子》当然没提到特朗普。但他在最后一章分析了这个美国梦幻灭世代的政治后果。他说,教育程度高和较富裕的公民比起教育程度低的贫穷公民,会更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具备更多政治知识,其结果是造成后者政治疏离感的扩大,因为弱势者会感到这个体制不能为他们说话、不能代表他们利益。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史蒂格里兹( Joseph Stiglitz)也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提到,经济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会相互恶化。
更进一步,这些疏离和冷漠的公民会变成一个个被动与分散的个人,一旦面对严峻的经济条件或国际局势,这些民众会呈现高度的不稳定,容易受到极端反民主的意识型态人操控。普特南甚至引用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一段话:“这些群众的主要特质不是残酷和落后,而是孤立以及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意思是,这个没有希望的世代很可能受到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这正是特朗普的社会基础。这群愤怒但保守的美国蓝领阶级遭遇的社会经济挫折是真实的,但是华盛顿的政治菁英却无能解决。因此,他们不信任政治菁英、痛恨华尔街,把问题怪罪给移民和少数族群。
另一大部分也深受社会不平等影响的年轻世代,则成为民主党参选人、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 (Bernie Sanders)的拥趸。

▲ 桑德斯与特朗普
五
怎么办呢?
普特南在最后一章尝试提出解药,主要是针对家庭结构、孩童发展和社区,是提升个人机会。相对于许多批判社会不平等的书强调1%vs.99%,普特南却在这本书中说没有“上层阶级的坏人”。他说:“对低新劳工来说,持续的经济复苏是我能想到的最好万灵丹。”
这样的立场遭到不少论者的批评,认为他并没有提出结构性的改革方案,如税制改革或提升最低工资。美国著名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认为,更有用的方法是回到普特南高中时的社会条件:坚强的工会和限制移民取得本国低薪工作。
当然,美国梦的破碎不是美国独有的矛盾,我们看到英国和欧洲各国也都面临人们对于不平等的不满,因此支持右翼本土主义,并且让英国脱离欧盟。
而在美国,特朗普真的会成为普特南的孩子们的代言人吗?
(本文原标题:《美国梦的危机与特朗普的崛起》)